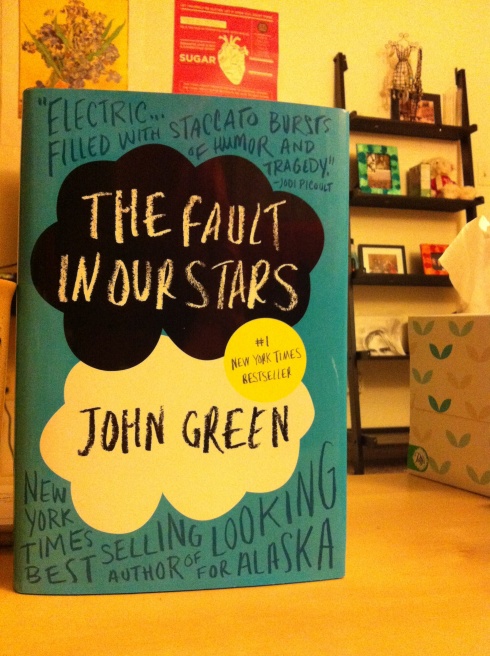差不多一个月前在Tea Leaf Nation上发了第一篇文,到现在为止写过的话题有在加纳的中国淘金者,网民对陈水总的反应,还有中国的同性恋人群。一开始只觉得写这类新闻评论是件有意思的事情,可以把我news junkie的本质和写作联系起来,作为工作之外的一个兴趣爱好,何乐而不为。但完成了第一篇,才真切了解到这个行当往往要求人去直面令人心寒的消息,不仅仅是浏览,而是深入的去探寻,并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机会,所以立马对做调查报道的记者们有了高一个层次的尊敬,特别是那些在这个行业里奉献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坚持的人们。两年前看屏风表演班的《京戏启示录》(李国修先生,RIP),最有印象的一句话就是,“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圆满了。”从确定话题到完成初稿,到来回编辑,再到定稿,差不多需要一到两天的即时跟进。如果我能坚持写下去,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吧。
过去一周多的时间都在波士顿参加哈佛公民与社会创新种子班,一个集结了一群希望用各类创新来促进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年轻人的项目。对于常年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我,想加入国内社会创新的队伍却又像没头苍蝇一般,申请种子班的初衷也是为了找到志同道合的组织。这初衷通过这安排满满的一周当然是如愿以偿,周四的总结会开得特别长,但是有些感受还是只能在稍稍沉淀之后才能化成文字。如果你是种子班的参与者和组织者,我想再次说声谢谢;如果你不清楚种子班是什么,我希望你能用几分钟的时间,看完我所写的,也去看看Harvard SEED的网站和微博,感受一下中国年轻人自己创造的理性正能量。
种子班开课的第一天,习惯了在办公室里敲电脑的我一下子认识了一屋子活得鲜活,踏实,接地气的人。安排好的讲座课程和小组讨论固然让人大开眼界,但是最令人受益良多的还是和种子班成员的私下交流。在我还在愿景坚持写新闻评论的时候,种子班有太多的参与者早已将坚持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
某天晚上分组讨论之前我和扎西坐在一起,因为在资料里看到她在去玉树前当过瑜伽老师,所以问了问她现在还有没有在做瑜伽。她告诉我因为玉树的天太冷,有快四千米的海拔,所以大多数时候冻得骨头关节生疼,舒展不开也没办法练瑜伽了,这次来美国顿时觉得筋骨放松了。扎西已经在玉树利民学堂工作了好几年,为藏区的失学儿童提供受文化教育和技能教育的机会。陈一和我的工作都属于能源环境行业,也都在国外留学多年。他在巴黎时参与创办“鸡鸣时”沙龙,为在巴黎的中国人创造一个讨论时事碰撞思想的空间,因为理性的空谈不会误国,而是一种集体成长。鸡鸣时沙龙两年前成立,已经举办了快70次活动。风趣幽默的田老师是回族人,是银川市穆斯林孤儿院的院长,长年为70个孩子的成长奔波操劳。他时常带我们在剑桥走街串巷去清真餐馆觅食,乐呵呵的把他们的院报塞给我们浏览。一帆和阿菜是种子班成员里的流浪派,一个已经走了42个国家,仍在路上昂首行走,但每天的预算不超过25美元,另一个行走于世界各地搜集社会创新的点子和故事,希望可以鼓励更多的中国年轻人加入行动的行列。
在种子班,梦想这个字眼会时不时出现。可是与梦想的宏大与美好相比,行动上的坚持才令人动容,而细节往往繁琐与冗长。坚持是扎西日日夜夜去习惯刺骨的寒风,是陈一和其他鸡鸣时的组织者每周都要解决场地问题,是田老师每天观察跟进孤儿院的孩子们,是一帆和阿菜用一颗好奇之心去面对接下来未知的旅程,即使是在被抢,被偷,感染疟疾之后,而这只是种子班所有人坚持的一个剪影。
社会创新实践是从一小撮人开始,但要做成气候,需要的是大部分人的参与。而要做到让其他人参与的第一步并不是向外放射性宣传,而是向内层层追问,这也是种子班课程里Marshall Ganz领导力课程培训中最重要的一课之一。要说服他人,必须得先经得住自己的追问:为什么你关心这些议题?为什么这个议题对你尤为重要?你现在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有没有哪些具体的事件和时间点对你价值体系的建立意义重大?而这个追问的过程,也许会触碰你试图忘记或不愿提及的过去,也许会让你沮丧烦躁灰心丧气,但只有抗住了这层推敲,才能更确定自己的信仰,才能提炼出自己的故事。而一个能让他人信任和受到鼓舞的真实故事,往往是撬动现状通往改变的必要条件。
过去的一周是一场不间断的狂欢,现在喧嚣暂停,在狂欢后的寂寞中继续前行,才是的我们集体修行的开始。种子班里的每个学员都有自己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需要继续跟进的社会创新项目,我们也许会产生摩擦和争论,也许完成目标需要的时间比我们的预期要长得多,但幸好过去一周的分享和交流让我们清楚的知道,不论过程有多艰辛,我们仍然是一个community,一个包容理性讨论,提供支持的community。第一天ice breaking游戏的时候和瀞仁互换信息,她是这么形容她自己的:“圆,温,软。因为我脸很圆,性格很温和,为人处事的方法也是软软的。”虽然是个声音柔柔的女生,但每次看瀞仁做安全照护的项目展示,总会以一种非常温柔的方式被信息的专业和理念的完整所打动。最后两天智行基金会的杜聪老师来做演讲,后来基本上SEED所有活动都有到场,不管是点评项目还是和学员们私下交流,也是走娓娓道来这种风格,不急不躁。我们这一场集体修行的终点,也许就是在实践中被打磨到温和且坚毅。
最近是毕业季,毕业演说词里总是充斥着试图给人打鸡血的字句。我最爱的一篇毕业典礼演说,是2005年作家David Foster Wallace在Kenyon College的演讲,里面并没有鼓舞人心的口号,但每年重读时,都让我有新的收获。他说,“成年人的生活看起来是由毫无意义的,一直重复的事件串联而成的,而人在面对日复一日的波澜不惊或是处处有那么点不如意的生活时,最容易的应对方法就是感到百无聊赖,去抱怨和发牢骚,而且感到自己不被幸运眷顾,这也是人的‘出场默认设置’。但是自由是需要被争取的,自由是清醒的反抗自己的‘默认状态’,是自主的去选择自己看这个世界的方式,而不是浑浑噩噩的一直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在这一周里得到的最大鼓舞,就是认识了一群正在清醒的选择自己看世界的方式的人,更是一群能把自己的思想付诸于点滴实践,有耐性去经历繁琐细节的人。
很多人说,等我有钱了,有时间了,我再来做和公益和社会创新有关的事情。也有人说,这个阶段我的投入产出比太低,所以还是等以后有能力的时候再做吧。种子班里遇到的各位,不管是学员还是组织者,都让我看到了参与方式的多样性,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那些积少成多的点滴实践在资源不宽裕时才更显难能可贵。不论你是种子班的成员,还是碰巧路过看到了这些文字感受,我们都共勉之。